男女主角分别是刘清宁王静的其他类型小说《两万里路云和月刘清宁王静结局+番外小说》,由网络作家“茹若”所著,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本站纯净无弹窗,精彩内容欢迎阅读!小说详情介绍:时隔十三年,当刘清宁再次踏进云上村,简直无法想象,这就是那个承载了自己童年无数欢乐的小村子。云上村大部分的老屋都是夯土墙、小青瓦的明清、民国建筑。一栋栋黄泥墙黑砖瓦的老房子,静静地伫立在群山环抱之中,墙角屋顶的杂草丛生。后山是成片翠绿的竹海,金色的阳光从云层后面泻下,在这一片翠绿色中显得十分清冷。村口两旁是成片的稻田,此时本该是是水稻生长的季节,如今却是一片荒芜。刘清宁记得小时候每到夏季,这里是一片翠色的水稻,到了夜晚,稻田里蛙声此起彼伏,她和吴楚楚就像两个小尾巴,跟在表哥们的屁股后面,在稻田里钓田鸡。月光下,风吹浪涌,绿波粼粼。她一不小心踩空,从田岸上摔进水稻田,裹了一身泥浆回家,外婆骂骂咧咧起床烧水给她洗澡,外公则抄起篱丝,满院...
《两万里路云和月刘清宁王静结局+番外小说》精彩片段
时隔十三年,当刘清宁再次踏进云上村,简直无法想象,这就是那个承载了自己童年无数欢乐的小村子。
云上村大部分的老屋都是夯土墙、小青瓦的明清、民国建筑。
一栋栋黄泥墙黑砖瓦的老房子,静静地伫立在群山环抱之中,墙角屋顶的杂草丛生。后山是成片翠绿的竹海,金色的阳光从云层后面泻下,在这一片翠绿色中显得十分清冷。
村口两旁是成片的稻田,此时本该是是水稻生长的季节,如今却是一片荒芜。
刘清宁记得小时候每到夏季,这里是一片翠色的水稻,到了夜晚,稻田里蛙声此起彼伏,她和吴楚楚就像两个小尾巴,跟在表哥们的屁股后面,在稻田里钓田鸡。
月光下,风吹浪涌,绿波粼粼。
她一不小心踩空,从田岸上摔进水稻田,裹了一身泥浆回家,外婆骂骂咧咧起床烧水给她洗澡,外公则抄起篱丝,满院子追着几个表哥打,打得他们嗷嗷直叫。
“说起来,外公外婆最疼的就是我们两个。”吴楚楚回忆起往事,无不感慨。每到秋天,收下的板栗,晒好的柿饼,外婆总要小心翼翼地藏好防备几个表哥,专门留着等她们俩放了寒假来吃。
山谷宁静旷远。
正是莺飞草长的季节,小路两旁的荒草茂盛,几乎要盖住水泥小道的三分之一。或许是清晨下过雨,水泥小道湿漉漉的,空气混杂着雨后潮湿与枯草腐烂的气息,毫不客气地钻进鼻腔,带着难闻的酸臭和沉闷。
一路走去,竟没有碰见一个人影。
“这村里到底还有没有人住?”吴楚楚忍不住咕哝。两个年华正好的年轻女子,跑到这样的荒郊野外来,不是聪明的行为。她心里有些发毛。
刘清宁没回答,担忧地看着周围荒芜的景象。
她可是在外婆面前拍了胸脯的,说老屋的事交给她来处理,一定让她老人家如愿以偿。外婆不信,问你大姨不同意怎么办?
刘清宁说,我爸妈都管不了我,她怎么管?我是成年人了。
老嬢嬢安心了,直笑,老树皮般皱巴巴的脸舒展开来,双眼也有了神采。可眼前这情形......
正发愁,身后“哐啷”一声,是门环撞击模板的声音,两姐妹齐齐回头。
朽到发白的木门被拉开一条缝,从缝里露出一张脸来。
九十年代电视上播《天师钟馗》,金超群演的,里面的钟馗黑面虬髯,怒目圆睁,两姐妹只敢捂着眼睛从指缝里偷看。
门后这个人,长得跟钟馗一模一样。
两姐妹“啊”地一声叫出来,吓得腿软,你拉我我扯你,跑出去几百米。停下来,气喘吁吁,面面相觑,说不出话,用眼神交流。
刚才那个,究竟是人还是鬼?
这光天化日,鬼怎么会出来?鬼怕阳光!
都二十一世纪了,说不定鬼也进化了呢?
瞎说八道!
两人会心一笑,定了定神,沿着记忆里的小路,继续朝村子深处走去。
王家老屋位于村子最深的西北角,因地势高,背靠后山,面瞰全村。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想象不到老房子已经破旧成这样了。
门前的院子,荒草已经长到半人高,水池排水沟堵塞,池水发黑发臭,已经是一池子死水。从前的房子没有卫生间,每天早晚,她和表姐两个并排站在水池边刷牙漱口,比赛着谁把水吐得更远,池水清澈,小鱼游得怡然自得......
正是蛇虫活动的时候,两姐妹不敢贸然踏进荒草丛,进不去,只能站在外头远远地看一眼老屋。
“记得那两棵树吗?”吴楚楚踮着脚,费力地辨认着,“以前我们总把吊床扎在这两棵树中间。”
“是啊。”刘清宁摸摸鼻子,“能不记得吗?”
两人相视,都知道对方想起了两人为了抢吊床打架,吴楚楚把刘清宁从吊床上掀下来,害她鼻子磕在地上磕出来血的事。
“那次受伤的,可不止你的鼻子!”吴楚楚搓了搓手心。
事后外公用尺子狠狠抽了她的手掌心,那是两人记忆里唯一一次外公对她们俩发火。
“哎,你看,那棵柿子树还活着呢!再过一个月,该开花了吧?”
“好像是。柿子树是五月开花吧?你记不记得那次,我们把柿子树的花都摘光了,气得外婆抄着篱丝满院子追我们打?”
“记得!”那年她们没能吃上外婆自己晒的柿子饼,就此长了记性,再不敢随便去摘果蔬的花。
物是人非,此情不再。
长久无人居住,老房子已经很残破了。
这老房子,还怎么住人?
花钱修吧?
要多少钱?刘清宁没多少积蓄。
她在马德里上的是智者阿方索十世大学,学费不便宜。家里不算富裕,但还是挤出了供她读书的钱,她心里本就有愧,加上与父母关系不好,更不愿意开口要生活费,半工半读,攒下一些。
不算多,但用来修这老房子,怕是远远不够。
自己可是在外婆面前拍了胸脯的。这些天,外婆的心情可真好,拉着那些来探她的亲友,不厌其烦地说等自己出了院,就要搬回老屋去住了,她的小外孙女要留下来陪她呢。
干枯的脸上焕发出油润的光彩,王美莲都说,多少年没看见老嬢嬢这么高兴了。
她得好好想想。
老屋的衰败让姐妹俩的情绪都有些低落,离开的时候,一路沉思,没注意到有几个影子已经尾随了好一会儿,听听到低沉的呜咽声,察觉到不对劲,一抬头,吓了一跳。
不知何时,几只大黄狗已经将她们包围。
两只左右包抄,堵住了两侧的小路,两只紧随其后,低吼着发出警告,守在前方的那只体型最大,耳朵竖立身体紧绷前倾,已经摆出了攻击的姿态。
刘清宁苦笑:“糟糕,这叫什么,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村狗相见不相识,嗷呜一声扑上来!”
两人还没开始笑呢,就听见背后有人鼓掌:“好诗,好诗!吴楚楚,几天没见,你文学细菌见长啊!”
刘清宁回头一看,是个年轻男人。
阿青婆生于民国初年,长于战争年代。具体的时间没有人记得,应该是1930年以后,她嫁到云上村,没几年,生下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那个年代,农村的日子并不好过,饥一顿饱一顿是常事。抗日战争爆发后没几年,阿青婆的丈夫,陈显华的爷爷陈定为了谋生,丢下家中的妻儿,跟着同村人一起去了欧洲,从此音讯全无。
那个年代青田人出国打工,并不走正道,死在半路上的人不在少数。
阿青婆等了又等,始终没有得到丈夫的消息,村里人都默认他已经死了,还有人劝她趁年轻改嫁,但阿青婆始终没有答应,独自一人将三个孩子养大。
那是个战争的年代,除了应对自然灾害,还要提防时不时从天而降的日军的飞机炮弹。
1942年,日军攻陷青田,云上村虽然偏僻,但没能逃过日军的搜掠。
“我父亲上了年纪之后,身体不好,常年卧病在床,常常同我讲起以前的事。”
那时陈建明已有八九岁年纪,他清楚地记得日本鬼子第一次进村搜掠,母亲带着他和弟弟妹妹躲进屋后的地窖里,年幼的妹妹忍受不了地窖的湿闷,大哭起来,引起了鬼子的察觉,
母亲拼命捂住了妹妹的嘴巴不让她出声才逃过一劫,等鬼子走了之后才发现,因为捂得太紧,妹妹已经闷死在母亲的怀里。
当时的情形在他幼小的心里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直到多年以后提起来还心有余悸,而母亲因为闷死了妹妹而愧疚,精神大受打击而病倒。
但即便病倒了,她还是得拖着病体下地干活,挣钱来奉养公婆,照顾两个儿子。
可以想见,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阿青婆过的是怎样艰辛的苦日子。
后来,红军打跑了鬼子,解放军渡过了长江,成立了新中国,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起来,大约是五十年代,阿青婆收到了来自西班牙的消息,原来陈定并没有死。
“这事村里人都知道!”李阿四说,“那年我还是个小后生,听我娘说,村里回来个华侨人,是阿青婆的男人,有钱呢!啊哟,不得了,穿西装,打领带,皮箱里都是洋货,后头那座石桥,就是他捐的钱修的,桥头碑上还有字嘞!嘿!原来那就是你阿公!”
那时云上村的人才知道,当年虽然陈定的目的地是欧洲,可是他上错了船,糊里糊涂地跟同村人分开,孤身一人被带到了南美,最后在巴西上了岸。
在巴西,他做过一段时间提包挈卖的营生。
所谓提包挈卖,是海外青田人积累资本最原始朴素的方式。
扛着一个编织袋,装着鞋子、衣服等杂物百货,一家一户地敲门兜售。那时候闯天下的青田人,没有人脉,没有门路,只能从最苦最累的活开始干起。
在提包挈卖的那段日子,陈定认识了一个当地华人的女儿,很快和对方坠入爱河,缔结婚姻。
在新岳父的资助下,两夫妻到了西班牙,开了餐馆,做大生意,赚了不少钱,成了大老板,又生下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听说了这个消息的阿青婆是什么反应,已无人知,但不难想象。
陈定在云上村住了半个月便走了,这一走就再没回来过。
后来陈定写信来,问阿青婆是否愿意出国,阿青婆拒绝了。
她收下了陈定寄回来的钱,推倒了陈家原本的破牛棚,重新盖了房子,便是现在的陈家老屋。
建新房子的时候,阿青婆只给自己在一楼留了房间,东西两侧各起了二层小楼,留给两个儿子一人一栋。新房建成,又大儿子陈建明娶了老婆,生了一儿一女,阿青婆的脸上,日日都是喜气。
她还有儿子、孙子,村里给她分了地,有田种,有饭吃,日子蒸蒸日上,没了男人,不算什么。
好景不长。
五十年代末,全国上下遭遇了大饥荒,到了六十年代初,生活变得更加艰难。
为了谋出路,陈建明带着妻子和弟弟,搭路子出国投奔父亲,也在西班牙定居,只留下五岁的大儿子和三岁的女儿,也就是陈显华的大哥大姐给阿青婆抚养。
阿青婆不得不又一个人承担起抚养孙子的职责。
70年代末,两个成年的孙子孙女也踏上了去西班牙的路。从此,老房子只剩下阿青太一个人居住。
“一直到新房子变成老房子,然后在这房子里孤零零地去世?阿青婆真是可怜。”刘清宁说道。
“其实,我父亲也想接她到西班牙一起生活。而且他确实也这么做了,在我十多岁的时候,奶奶来过马德里,还住了一年,所以,我对她有一点印象。”
在陈显华的印象中,奶奶是一个非常古怪的老人。
她一直穿着很旧的蓝布衣衫,是那种传统的中国样式,衣领袖口还绣着中国样式的花纹。
她不会说普通话,更不会说西班牙语,而是讲口音很重的青田方言。
那时候,陈显华不会青田话,如听天书一般,根本无法与奶奶交流。
阿青婆被接到马德里的时候已经年迈。
那时候,陈显华的祖父已经去世,他的继奶奶是陈家的大家长,在马德里,她唯一认识的只有自己许多年未见、并不熟悉、忙于生意的两个儿子和由自己抚养长大的两个孙子孙女。
听到这里,刘清宁忍不住想起了刚到马德里的自己。
当初登上前往西班牙的飞机,阿青婆肯定和她前往马德里之前一样,是对未来的生活抱着一种期待的,她盼望的是与从未谋面的父亲、分离多年的母亲的重聚,期待的是父母疼爱的怀抱,阿青太盼望的、期待的则是母子团聚,一家团圆,从此颐养天年。
但很显然,她们都没能如愿以偿。
父母疼爱的怀抱,是属于她的弟弟妹妹的。而一家团聚颐养天年,则是属于那个抢走阿青婆的丈夫的女子的。
长久的分离,文化的隔阂,是她们和家人之间迈不过去的鸿沟。她们都成了这个家庭的“旁观者”,就像西方电影里那种死去之后留在家里的亡魂。
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并不愉快。
“奶奶应该也开心了一段日子的。”陈显华说。
初到马德里,阿青婆在孩子们的陪伴下游览了这座陌生的城市,但当最初的新鲜感褪去,面对忙碌的孩子们,她开始思念自己的小村子。
“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不能一直陪着奶奶。而奶奶不会说西语,也不会说中文,在马德里根本不能独立生活。”
没过多久,她就只能日复一日地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望着窗子发呆。
有时候她会做一点针线活,但是她年迈眼花,针线活做得很差,缝出来的东西,也根本没人愿意用。
她还很简朴,那些废纸盒、旧塑料袋,都会被她如同宝贝一样收起来,藏在自己的房间里,将一个小房间塞得满满当当,异味刺鼻。
对此,孩子们提出强烈的抗议,多次爆发了争吵,虽然这些争吵用的是西班牙语,但是语气和神情,奶奶听得懂。
这些都是陈显华长大以后回忆起往事,才品味出来的。
没多久,她就提出要回国,态度十分坚决。拗不过母亲,陈显华的父亲只得将她送上了回国的飞机。
回国之后没几年,阿青婆就去世了。
现在回想起来,刘清宁幼时记忆里的阿青婆,就是在马德里小住了一年之后,带着失望、遗憾、苦痛回到老屋的阿青婆。
“奶奶临走的时候,身边并没有亲人。她也没有留下遗书”或许是因为她不知道她的遗言该与谁说,又有没有人会回来读她的遗书。“但是我想,奶奶是很希望我们能回国来看看的。”陈显华说,“因为她离开马德里的时候,留了这张照片给我们。”
他指了指桌上的那张泛黄的老照片。
刘清宁拿起相片。
路寮里灯光不亮,照在泛白的黑白照片上,显得越发的模糊。
照片里的阿青婆,比刘清宁记忆里要年轻许多。拄着拐杖,站在陈家老屋的前面,郑重地留下了一张自己与老屋的合影。
“这张照片,是阿青婆去西班牙之前拍的。”王永梅摩挲着照片上的阿青婆,“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不像现在,照一张照片不容易。阿青婆一辈子没拍过照片,就那一次,请村里照相馆的师傅来给她拍的。她说自己这一走,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回来。在中国,她没有家人、没有亲人,她放不下的只有这栋房子。”
是啊。那个年代农村人盖房子,一梁一柱,一砖一瓦,都凝聚着主人家的心血。
刘清宁想,当初盖起这栋房子的时候,阿青婆对生活还是带着期盼的,即便那个男人离开了她,她也还有自己的日子要过,她期盼孩子能在自己的身边长大、结婚,生子,儿孙满堂。
谁知她的儿子、孙子,一代又一代的人,陆续地离开她,远赴重洋,再不回来,她对未来的期盼便一次又一次地破灭了。
直到她从马德里回来,她的心便彻底死了。
老人们传阅着那张发黄的旧相片,谁都没有说话,只是不住地叹息。
王永梅回忆:“阿青婆走的时候,身边一个人都没有。那天早上我起来,远远地看见她坐在家门口那把椅子上。”
刘清宁记得,阿青婆最喜欢坐在门口的那把椅子上,伛偻着腰,穿着蓝布衣裳,花白的头发盘在脑后,一丝不苟。
偶尔有人山上干活,路过她家门口,便停下脚步与她聊上两句,讨口水喝。村里的孩子打闹着从她家门前经过,她就乐呵呵地打招呼。
“娒,别跑,要扑倒的!”
夏天,手里摇着蒲扇,冬日,怀里抱着暖龙。山中时日须臾过,她岿然不动。
“我没在意,照样去喂鸡。快到中午的时候,她还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我以为她睡着了,怕她冻着,就去叫她回屋里睡,没想到......她已经走了。”
她一定是知道自己要走了,早早地起床梳洗打扮好,坐在自己最喜欢的竹椅上,静静地眺望着远山,阖然长逝。
远山之外还是山,重重叠叠的远山之外,是她再也不会回来的亲人。
—
“是啊,阿青婆走的时候,你们家没有一个人回来。也没人知道怎么联系你们。村委会只好做主操办。我们都去帮忙了。”李阿四回忆道。
这事陈今越听李阿四提过。阿青婆走的时候,陈家没人回来,那个年代通讯不方便,交通更不方便。没办法,村委只好出面操办,发动村民凑钱出力,将老嬢嬢的身后事料理妥当。
李阿四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十分气愤。
“亲娘死了都没一个人回来,这就算来了,这十来年了,也没见一个人回来扫墓的。这一家子真要遭雷劈。我还垫了两百块钱,这下拿不回来了!”
提起自己垫的两百块钱,他捂着心口直跺脚。可如今再提起来,李阿四仿佛已全然忘记了那两百块,只有愤怒。
陈显华有些窘迫地点头:“是的。我们得到奶奶去世的消息的时候,奶奶已经安葬了。本来我爸爸说要带全家回来拜祭奶奶,但是那时候我父亲的年纪也不小,身体不好,家里生意也忙,一等再等,后来......”
“就再没回来的必要了。”刘清宁冷冷地说。
陈显华没说话,算作默认。
他不得不承认,对于这个奶奶,他根本一丝感情都无。
奶奶在马德里居住的那两年,他还是个孩子。
一个十多岁正值青春期的男孩子,全部的心思都在足球场上,对于奶奶的出现、离开、直到去世,他都没有太多的关心,甚至对这个无法沟通,奇奇怪怪的老嬢嬢感到厌烦。
奶奶回中国的时候,他甚至还欢呼雀跃,因为家里终于不会再出现那些散发着酸臭味的旧纸箱子和塑料袋,也不会被父母逼着用那些奇奇怪怪的针线,只是为了怕奶奶伤心。
从前并不觉得,如今在这群与奶奶相识的故人面前提起来,在他们的目光审视下,他忽然觉得坐立难安。
路寮里一片静默。
两位老嬢嬢不住地抹眼泪,阿太摇着扇子直叹气,李阿四呢,坐在门槛上,铁着脸,不说话,脚下的烟头摁了一地。
认识李阿四半年多,陈今越从来没见过他这这幅模样。
“喇叭四”不响了。
“那你怎么突然又想起了回来探亲寻根?”陈今越打破沉默。
陈显华紧张地舔了舔唇,看了看其他人。
只有刘清宁看着他,一双黑漆漆的眼睛映着路寮昏暗的灯,那灯只有光秃秃一个灯泡,用一根电线吊在半空。晚风穿堂吹过,灯泡在风里晃,映在她的双眼里,就像跃动的火苗。
“我成年之后,继承了我父亲的生意,经常需要在各国来回奔波。三年前,我因为生意上的事情去利比亚出差。”
陈今越立刻想到了:“也门撤侨?”
“是。”
2015年初的也门撤侨,中国的3艘军舰,从也门撤出了613名中国公民和279名外国公民。
“我就是那279人当中的一个。”陈显华说。
那天他登上中国的军舰,军舰上挂着鲜艳的红旗,旗子上有五颗星星。和他一同登上军舰的中国公民手里挥舞着同样的小旗,唱着他听不懂的歌。边上有一个罗马尼亚人用力地拥抱了他,用中文对他说了一声“谢谢”。
那是第一次,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与中国血脉相连。
“所以你就决定要回中国寻根?”陈今越问。
“是。”
他突然对自己这个素未谋面的祖国产生了强烈的好奇。从那以后,他开始留意关于中国的新闻,开始接触身边来自中国的华侨,也会开始询问父母关于他们从前在中国的一切。
“从他们的嘴里,我听到了许多不同的中国。我不知道哪个是真的,所以我决定自己回来看一看,看一看我的我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都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这个他从来没来过,但是却与他血脉相连的地方。
故事讲完了。
陈今越站起来:“走吧。”
“去哪儿?”
“去那个与你血脉最相连的地方。”
这是浙西南的一个小县城,八百里瓯江从这里穿流而过。
清晨的薄雾散去,宁静小山城渐渐喧哗起来。这个时间,菜市场是最热闹的。
今晚家里有客人,王美莲特意起了个大早去菜市场买菜。她挑挑拣拣,在家禽摊上看中了一只鸡,付钱的时候才发现钱包不在包里,只在夹层里搜出一张100元面值的欧元,“这还有张欧元。”
大概是过年的时候,哪个亲戚塞来的孩子的压岁钱。
王美莲将欧元递给老板娘。
老板娘爽快地接过欧元:“今天汇率可不好,你不划算哦!”说着麻利地找了钱。在这个“家家有华侨、户户有侨眷”的小山城,连卖菜的阿姨都对欧元的汇率变化了若指掌。
买了鸡,又买了两斤河虾,鱼,茭白和一些青菜,拎着买好的菜,王美莲扭头转到新大街上。
县城不大。
瓯江自西北往东南奔涌而去,小镇便在瓯江一侧依江而建。两条自西北往东南的路,一条依山,一条傍江,将县城围成一个两头尖的橄榄形状,新大街正在橄榄最宽处,将两条大路联通。
新大街全长不足300米,却银行林立,被称作“侨乡的华尔街”,最拥挤的,总是中国银行营业厅的大门口。
与美国华尔街里西装革履的精英不同,中国银行的大厅里、门口聚集的都是一些穿着朴素、甚至还拎着菜篮子、刚刚从菜市场买菜回来的老头老嬢嬢。
他们的兜里揣着欧元,眼睛紧盯着银行大屏幕上显示的欧元汇率。遇到汇率好的时候,中国银行柜台前排队兑换欧元的队伍排出十几米长,银行经常要连续营业二十几个小时来满足他们兑换的需求。
这些老头老嬢嬢,大多数都有一个、甚至几个孩子在国外,大部分是欧洲,美洲,澳洲,中东也有。孩子在外打工做生意,将挣到的欧元寄回来,他们在国内则担任起“财政总管”的角色,等待汇率高的时候将欧元兑换成人民币。
或买房,或供留在国内的孩子上学吃穿。
这番景象,与这个刚刚脱贫不到十年的中国小县城格格不入却又融合得无比妥帖。
这里是侨乡,浙江青田。
夕阳西下,夜幕将临,下课铃声响起。
刘清宁骑上自行车,与同桌挥手道别,约定晚自习她带一整张刘亦菲的贴纸,作为自己刚刚给她讲解数学试卷上最后的那道大题的“报酬”。
2005年,《仙剑奇侠传一》热播,刘亦菲的贴纸是学生之间的硬通货。
初夏的傍晚,夕阳的余晖依旧刺眼。自行车飞驰在乡间崭新的水泥路上,道路的两旁是郁郁葱葱的稻田,在晚风里,如绿色的浪一般。
在马德里的很多年里,临睡之前,刘清宁常常会想起这一天的夕阳,和夕阳下的麦浪。
回到家,大姨王美莲已经做好了晚饭,满桌子的好菜,大姨父正跟一个男人坐在桌旁喝酒。
这个男人刘清宁见过,大姨管他叫“林老板”,她爸妈当年就是走了林老板的路子出去的。林老板出去的早,在外面早就拿了居留证,赚了许多钱,表姐读的高中最好的那栋教学楼就是他捐钱盖的,用他的名字命名,青铜大字挂在教学楼上。
1993年,刘清宁还在她妈王静肚子里的时候,她爸爸刘万信就搭了林老板的路子,上了一艘前往欧洲的货轮。1995年,刘清宁2岁,她妈妈将她交给了大姨,也登上了前往欧洲的轮船。
大人的事她知道的不多,但从大人们的对话里也能知道一二,知道她爸妈先在荷兰团聚了,后来又听说进了难民营,因为没有居留证,是黑户。再后来,他们辗转去了马德里,还给她生了一个妹妹,因为这个妹妹的出生,又适逢西班牙大赦,他们拿到了西班牙的居留证,从此在马德里定居下来。
从懂事开始,她就知道未来会有这么一天,她会告别中国,到父母的身边。
但这一天来得如此毫无预兆。
“快去吃饭,吃完饭洗个澡。”大姨推了她一把。
2005年的初夏,一个平淡无奇的傍晚,刘清宁从浙西南这个小镇子出发,先坐一晚火车到了上海,从浦东国际机场登机,坐上了前往西班牙马德里的飞机。
一别十余年。
从青田到马德里,从此云与月相隔两万里。
李阿四热络地给三人添茶:“小陈镇长,这是镇里新来的领导?”
吴楚楚道:“阿四叔,你不认识我?我是美莲的女儿!”
李阿四一拍大腿,眯起眼睛想了一会儿:“哦哟,永梅姨的外孙女!是吧?”
“是。”
“上次在向远店里见过嘞!”
“没错。去年还是前年的事了,你记性真好。这是我表妹,宁宁。”
“哦,宁宁阿囡!小时候见过,我还抱过你呢!”
知道是熟人,几个老人迅速热络起来。
躺在竹摇椅里悠闲自在地摇着扇子的老嬢嬢,年纪不大,中等身材,白面皮,短发烫着小卷,染着和眉毛一样的红棕色,耳朵上挂着两个金晃晃的耳坠子,财气十足。
两姐妹不认识,李阿四介绍,是位归国华侨。
年轻的时候出去闯,辗转南洋,欧洲,最后在巴西住了三十多年,普通话都说不好,却会说一口流利的巴西语。听说她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在巴西,生意做得很大。
“我今年才六十五,年纪小辈分大,你外婆都要叫我姑呢。你要叫我阿太了!”老嬢嬢说道。
“你们该叫她姑婆太!”李阿四指点着。
两姐妹顺从地叫了一声“姑婆太”。
角落里的睦竹椅上坐着一个瘦小的老嬢嬢,穿着一件老式的蓝布衣,从三人进来开始就没说话,只是微笑。
李阿四介绍,这是万斋婆。
刘清宁想起来了,万斋婆是万斋公的老婆,万斋公是一个高大的老头子,教了一辈子书,退了休没事做,日日在路寮跟人闲谈、下棋。
云上村的孩子们玩闹,看见万斋公坐在路寮里便远远绕开,因为一旦被他抓住,他就要摇头晃脑起来:“娒儿,几年级了?我来考考你......”
后来万斋公走了,万斋婆就一个人过日子。听说她生过几个孩子,都死了,好不容易养大了一个,90年代跟人出国,再没有消息。
听外面回来的人说是死在半道上了,但没人敢告诉她,只说联系不上。
下山的时候陈今越告诉姐妹俩,自从小儿子也没了,老嬢嬢的精神就有些不正常,有时候一天到晚一句话不说,只是笑。
两人童年的回忆,随着与几位老人“相认”,全从记忆深处不住地冒出来了。
“阿太,你家人都在巴西,你怎么不留在巴西?”刘清宁问。
阿太躺在摇椅上扇着蒲扇,半睡半醒的样子十分惬意:“巴西哪有家里好?我住不惯那个地方,也吃不惯那里的东西。年轻的时候要赚钱没办法,后来又要帮儿子带孙子,没办法。”
“你不知道,她有二十多个孙子外孙嘞!”李阿四插嘴。
二十多个,刘清宁听着都要晕过去了。
“可不是吗,带了孙子又带重孙子!现在老头子不在了,我一个老嬢嬢,是该休息的时候了,他们生个不停,我可带不动了,我就逃回来了!”
哄堂大笑。
阿太在摇椅上挪了挪身子,找了个更舒服的姿势:“回来好啊,家里吃好喝好,病都少了,这才叫好日子呐!”
“这话没说错!”李阿四十分赞同,扯着大嗓门发表意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和种田一样的,我们南方就种水稻,他们北方就种小麦,我们南方硬要种小麦,那肯定水土不服!我们中国人就该长在中国的土地上,吃中国的土地种出的大米蔬菜,身体就会好,病就少了!”
“那你不想孩子吗?”
“想啊。哎,但是没办法。我说让他们有空了回来看看我,都说好好好,结果呢,你看看,我回来都五六年了,一次都没回来过。”阿太叹气,“哎,年轻的时候呢,我们为了赚钱去国外,把孩子们丢在家里,也是几年回不来,现在老了,风水轮流转喽!”
她说完便轻轻地笑起来,摇着蒲扇和摇椅,仿佛十分惬意的样子,但那语气中一丝丝的遗憾,随风飘散之际,却被刘清宁敏锐地抓住了。
李阿四弓着背,拎着茶壶从屋里出来,给几人都添了茶,嘴里念叨:“子女缘天注定,跟我们两个比,你算好的了。”
“好什么,殊途同归,现在都是孤单单一个。”
“有我们两个陪你呢,不算孤单。”
众人都欢乐地笑了,安静地坐在一旁的万斋婆也轻轻地笑出声来。刘清宁端起茶碗,这次没有一饮而尽,而是小口小口地品着这苦中带甘的滋味。
喝着喝着,突然觉得不对劲,背后发凉。
“阿四叔,这村里现在就住了你们三个?”
“没错。”李阿四比划着,“我们三个现在是相依为命。”
两姐妹对视一眼。
那么刚才看到的那个,还是鬼?
山谷寂静,山风拂过山岗,穿过路寮,从后颈的衣领钻进去,禁不住打了个冷颤。吴楚楚咽了咽口水,无声唱起歌来。
从前看完恐怖片晚上不敢睡她就唱这个,管用。
陈今越看了看两姐妹的样子,料定她们两个刚刚撞见过老吴了,敲了敲桌子,笑:“阿四叔,你别胡乱说话,吓得她们两个脸都青了。那后头的大宅还住着一个,这村里现在就这四口人。”
“噢!”两姐妹擦了擦鬓角的冷汗。
李阿四硬着脖子:“你当他村里人,他自己不认呢!”说完又低声嘟囔:“这冷屁股要贴你自己贴,我不贴。”
阿太摇着扇子:“你别同他说,他们两个有私怨。”
“谁跟他有私怨?是他对不住我,骗光了我的养老钱。嘿,老天爷也看不下去,让他儿子跟他断绝父子关系......”
“行了。”眼看对方越说越不像话,陈今越不得不端出架子,正色道:“李阿四同志,你现在是村里的网格员,也好歹是半个政府的人了。面对群众,怎么能夹带私人情绪?”
“政府的人”这四个字,显然让李阿四很受用。刘清宁注意到,陈今越说出这四个字的时候,尽管脸上还很是不服气,嘟嘟囔囔地小声反驳,但李阿四的胸脯不由地挺直了,昂头挺胸,十分骄傲。
她忍不住噗嗤笑了。
临走的时候,阿太拉住陈今越问:“小陈镇长,前头我和你提的老人食堂的事,镇里有消息吗?”
陈今越耐着性子解释:“阿婆,我同你讲过了,你们就这么几个人,搞老年食堂不现实。就算你肯出大头,这点钱也办不下来。不如你听我的,搬到山下去住。”
阿太摇头:“我不去。我要住在自己家里。”
陈今越无奈:“那你自己小心,阿四叔,万斋婆,你们都是。隔夜的饭菜要少吃!”
“知道,知道了。”
“你们就敷衍我!”
回去的时候,三人沿着山路拾级而下。
正午的阳光炙热,山脚下是一片粉墙红瓦的新楼,鳞次栉比,反射着刺眼的日光。青山如黛,一切都是崭新的模样,这种新有一种蓬勃的生命力,让人心情愉悦。
与这山脚下崭新的、蓬勃的新村庄相比,山上的云上村显得更加衰败。
在不久的将来,这个承载着她童年快乐记忆的小村子,或许就要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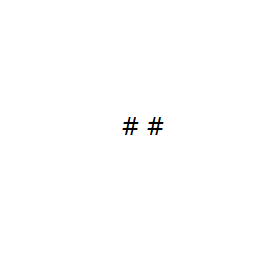
最新评论